午夜的港口,枪声叫嚷声连成一片,父亲带着我穿过一具又一具的尸体,鲜血浸透了我的衣服,本来保护我们的保镖都倒在了走向码头的路上,最后留下的除了我跟父亲还有nineteen——我的教导官。
本来易月生是与我们同行的,不过半路出了变故,他急匆匆赶去处理,把人都留下了。我一直好奇究竟是什么事能让四平八稳的易月生如此惊慌失措,后来我才明白,是他的猫不见了。
一群白面具如潮水一般涌了过来,nineteen和父亲势单力薄,被逼的节节败退,他们似乎不想要我们的命,只是不断的缩小包围圈,教官命令我闭上眼睛,不准看眼前的尸山血海,不想让我看到父亲跟教官杀人如麻的模样,可是遍地鲜血,看不到并不代表我不会胡思乱想。
我的人生十二岁是一条分水岭,十二岁之前我是父母手心里的宝,教官对我严厉不乏爱护,除了偶尔被教官打,顺风顺水地长到十二岁,只不过人生如戏,突生变故。
那时候父亲跟教官已经支撑不住了,教官挺拔的身姿佝偻了腰,父亲已经扔下了枪,换上了刀。白面具涌上来,父亲跃起,刀光闪过,可惜寡不敌众,白面具的子弹比他更快,瞬间穿透了他的胸膛,我想要扑上去,教官拉住了我的手,往后一退,然后我就看到教官倒在我面前。
教官有一双亮如星光的眼睛,年幼时我曾问他为什么他的眼睛那么亮,教官看着我温和地笑“因为眼睛里有光明,所以别人看到的眼睛是亮的。”那时候我很小,穿过大半个小城去教官的家里,他教我读书写字,我听他讲故事。然后日暮西风,他会送我走到那条小巷,说一句“黄小姐,小心。”教官极少叫我的名字,常被他挂在嘴边的就是黄小姐。
说来很奇怪,我父亲姓焦,母亲姓张,而我姓黄,每逢自我介绍的时候总有那么一句,“我姓黄,蟹黄的黄”感觉很别扭,仿佛这不是一个姓,而是一种铭记的手段,似乎只有这样,有些东西才不会烟消云散,湮灭如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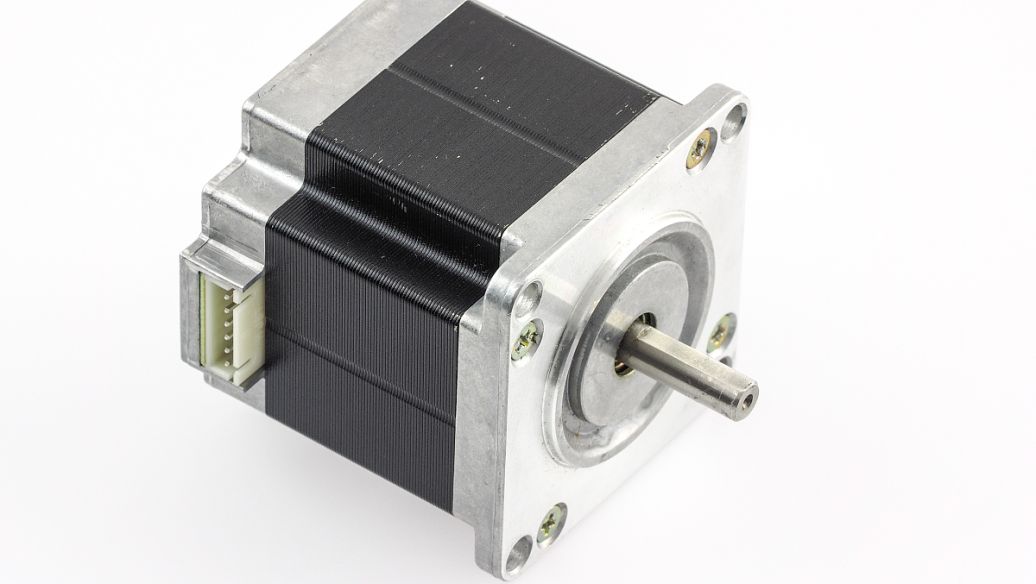

 洛涟
洛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