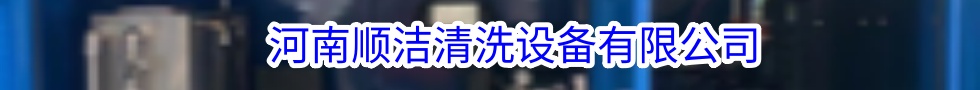一:这头牛大概是神仙
夏日炽热的阳光豪纵得在天地间奔洒着,无影的热情洒落在稻子上,洒在一眼无垠的绿油油似要滴出水的稻田上,叶子的腰身顶部都镀上了点水腻腻的白金色的光,放眼看去像是铺了一地的碎钻石似的。田垄上边儿高到人腰部的野草从晃悠悠着随风摇曳,有似人在路边散步时的闲适惬意,风漫不经心得在裂缝横生的水泥路上行走,和路两边的野生花草打招呼,几只小小蚊虫在花草间玩捉迷藏。
午后时分是九门村最安静的时候。日头毒气温高,出了门在太阳底头,一种被放在炉上烤似的火热感就浇了个遍,浑身难受。除了去十几公里外的市场采货,拜访别家邻居或别的些事外,村里人大多不出村,大人在家里看电视或者躺在竹席上打盹儿,又或者拿芥菜白菜萝卜出野草路边晒。小孩就奔到树荫大伞下,一伙人搬来两拳又两拳的石头,在地上画个歪歪斜斜的圈圈,然后开始比赛扔石进圈,扔中次数最多的胜出。如果这个游戏结束,一伙人又去谁的家里拿条细长的橡皮绳,将人分成两组后各派个代表,用脚撑着绳子成四边形,两拨队根据不同样式来跳花样绳,哪组人跳时踩绳的最少就算赢。诸如此类的集体游戏,虽然简单,不过是胜在群体一起游戏的愉悦快乐。
这村里头有张幽绿阴阴的池塘,塘边围着一张叉形铁网。在万丈光芒照耀下,水面下的块状青苔随同风荡起的涟漪自由自在得游玩,有时能看见附在上面的嫩粉色蛇卵,再细看,会有几条身子泛着点点碎碎磷光的草鱼鲫鱼,轻浮得骚弄着鱼尾巴,走秀似得漫游在铁网下方的水草丛里。
再过两三步,与池塘隔着一条草间沉泥小路,站立着一张緑铁网,网后一个偌大矩形篮球场,地上屎迹斑斑,大多是隔壁几户人家的母鸡或者鹅鸭来游走时排下的。稀罕些的一两大坨黑不溜秋的牛屎,估摸这是傍晚时分,老农夫牵着老态臃肿的田牛慢悠悠路过这里时,瞅着没什么人,就让牛在这里排粪。反正来这里唑唑走走的人都不介意地上的屎,甚至有时他们谁光脚踩着了,脸上也是一派云淡风轻,仿佛踩的那是块棉花糖。
日光正盛此时,一头毛色乌黑亮丽,体魄雄健厚实的田牛伏在篮球场的阶梯下比较干净的区域闭眼休憩着,白光在它身上肆意得游走抚摸,黑色短毛发上闪着一层薄薄的白星光,细长的尾巴贴着股肉上边儿,四爪子绻在肚皮下,在热辣的空气下显出些温和缱绻气氛。篮球场角边的树林阴翳下,夹在树叶间隙的不规则日影往躺下面的人身上扑落而下,撒娇般依偎在他怀里,好似一个处在热恋期的人在亲昵得拥抱着他,亲吻着他裸露的麦色肌肤。
清风悠悠缓缓行驶着,那人身上的流影随风而动,兜了兜转了转,却旖旎得不肯离开。
“唉。”晒死个人了。吴邪满脸憋屈得皱着张脸,拿过盖在脸上的草帽拍着自己的腹部,眯着眼,感受那经了树荫过滤却还如火烧似的热浪。没一会儿,他眯开眼瞄了那边在曝晒的黑田牛,忍不住又叹了口气。
平日里这头牛很乖很听话,乖巧的程度高深到了让人怀疑自然与科学的地步。比方说,吴邪叫他走哪儿它就往哪走,指东就是东,指西就是西,方向都不带点儿偏斜;让它待在哪儿它也会十分乖巧得伏在哪儿,任谁来拉它都岿然不动,坚执得要命,好像吴邪的话不是个简单的命令,而是个几千斤沉重的守护责任般,惊得吴邪以为自己做了什么无意识的举动伤害了它精致的牛皮心灵,着实让人心慌要紧。
然而今天这头牛难得任性得自个走出那片阴凉的牛棚,体态臃肿迈着优雅的小碎步踱到篮球场这边,牛头转得跟摄像头街抓拍般缓慢又机械,瞅着一点没被粪便侵袭的区域,踢了两蹄子后缩起四肢伏在上儿,好像今天天气日头和煦空气凉,空气中那气流在浮动幻成波浪状的玩意儿不存在似的。
不管那头牛是否真的不知人间冷暖凉热,吴邪无奈憋屈中还是很担心它会中暑,他跑到那黑田牛的旁边蹲下来,把草帽往那牛头遮,一片带着点点闪光的圆形阴荫在牛头上映成了个不规则的阴影,黑田牛睁开眼睛看着吴邪,那对平时目不转睛的黑眼眶里多了点眼白,透着股询问的微妙意味。
“我们回去吧?这儿太晒了!”黑田牛闻言事不关己似得闭上眼,吴邪认命得撅起撇向一边的嘴,手搭在黑田牛头上,手指轻柔得扫过牛耳朵,脑袋低歪下来跟牛眼睛相平,好声好气道:“唉呀,你要是中暑歇菜了,爷爷可没哪个精力带你看大夫,来嘛。”
黑田牛动了一下耳朵,没有任何要起来的征兆。吴邪蹲着,地上正在向上空散发着一层层波浪状的热气,正烘烤着他的屁股,他感觉屁股连着大腿处的裤子被汗浸湿了,脑门脖颈也在蹭蹭冒汗,他抹了把脸上的汗水,瞅着眼前一毛不拔的黑田牛,他再一次重重地叹了口气。
牛神仙脾气还挺球儿大的嘛。
(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