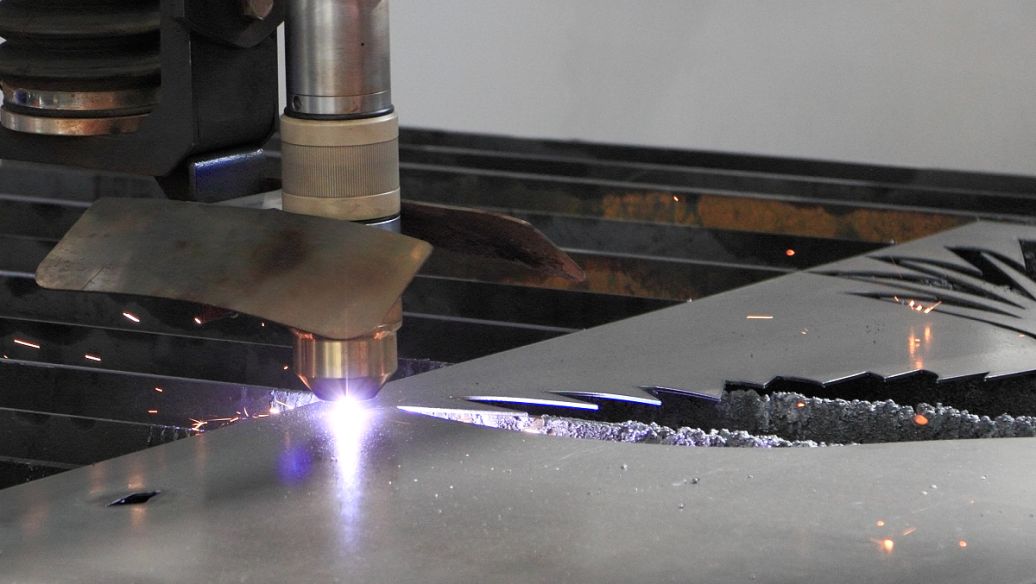论史记不应是美化项羽的文学小说,而是诠释汉室合法统治的长篇正传,
项羽之所以能作为中华历史上少有的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君主式人物,许多人的意见都是认为司马迁个人对以妙笔生花的文笔对项羽进行的过度溢美。
事实上从结论上看,恰恰具有一定程度的捧杀嫌疑,首先从写作背景上可以参考下司马迁与其父辈的出身,由司马迁生父司马谈临终前对作者的一番叮嘱就可见一斑:“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他希望在死后,司马迁能继承他的事业,更不要忘记撰写史书。
如果有人认为司马迁写书是可以不需要诸多考量斟酌的,要知道史记是包含了众多人物,规模与信息量都无比巨大,不可能都来自司马迁一人之所想,其本身也是根据已成书的楚汉春秋编纂而成,绝非他的一夜独创,自然有不少可以修改加注的余地。
加上史记在后世明显有被刘向等人在东汉时期删改过的痕迹:
《后汉书。杨终传》:“终又言:“宣帝博征髃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焉。会终坐事系狱,博士赵博、校书郎班固、贾逵等,以终深晓春秋,学多异闻,表请之,终又上书自讼,即日贳出,乃得与于白虎观焉。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
从这里可以引申出一个绝非可以忽视的问题:无论史记的作者是不是司马迁,他写了多少文字,它要想存在和流传都必须通过刘汉政权的检查和认可,都必须修改到符合刘汉政权的立场。而这种立场以视为从历史的角度证明汉政权是合理合法合乎天道和天意的。
不是说史记就不能正确地反映历史真实,而是说要如何认识和看待它是怎样反映历史真实。
就其属性而言,史记无疑是当代史,是一个片面性的单方面的证词。不是不可充当证据,而是不可以将其当作史观的指导,因为史料本身就是理解的历史工具而不是唯一的证据,更不可代替史观本身。
单单就解读项羽本纪本身,就很清晰地说明了关中之约与以义帝之死发动讨逆战争的理据合法性,对于刘邦成功获取权力地位是作出了最关键的支持,而刘邦为了得到顺利继承帝制的结果,先要描写暴秦解体的直接原因,再完美诠释一个自己为何会承袭帝制的过程。
为这政治格局的变迁之中寻找一个最佳的平衡点,项羽西楚政权的存在无疑是最佳的转折点,要承袭暴秦制本身,为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就必须将项羽分封的行为证明是历史的“倒退”,从结果上瓦解分封的意义,让灭秦之功顺利转嫁到另一个成功者身上,变成继承秦制的最正当理由。
而项羽一生征战的过程,在本纪中通篇的文字里,凡是读者都很容易从多个角度找到他失败原因的一些“证明”,如残暴不仁,政治短视等,
与刘邦的对比下,项羽当时的地位无形中被高估,如鸿门宴中不少人都认为他可以直接消灭刘邦,应该直接王关中等,
也导致其能力被间接性的低估,尤其他的政治能力与谋略智慧经常被忽视,乍眼一看就好像“鼠目寸光”,很多的抹黑之词如沐猴而冠彪悍滑贼之类,也是由司马迁引用各种佐证穿插其中的安排而显得“情理之中”。
结果同样掩盖了刘邦集团同期也曾制造过的暴行,甚至可能只是一种转嫁的结果,
如秦宫的财宝最后不知所踪,始皇帝墓被盗,等等事迹。
项羽在记载上失德的每一点几乎都为后面的高祖本纪里汉高祖的成功作出诠释或注脚,这正是最精心细致的巧妙铺垫。
从灭秦之功到所谓的残暴失德,再到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只得出了欲以力征经营天下这样的苍白定性。
由此可见,真正高明的做法,不是通过对成功者大书特书的赞美,
而以适当展现失败者的种种得失成败的对比手法,作为客观真相的某种“体现”,再借此突出自己的豁达大气,包容并蓄的作风。
那些带有感情色彩描述的项羽事迹,不论是儿女情长还是优柔寡断,在当时的历史眼光中更是让他丧失了身为政治家的合格地位,留下匹夫之勇这样普通读者最容易得出的刻板印象,
从一些专门讲述男女之情的文学作品地位一贯低下就可见一斑,强调项羽重情的笔墨未必就可以跟美化等同。
至于其他细节上的表现,对他军事能力和武力上的表现,真正被隐藏战绩的应该是项羽,而不是刘邦,从法理上讲,隐藏刘邦战绩是严重污蔑,等同欺君之罪,在当时的统治环境中也没有可以实现这种暗箱操作的条件可言。
同样的七十余战,同样为帝制统治作出重大功劳的白起就显得更为耀眼立体,详鲜明细。
再联系到汉武帝执政时期对异见者的打压,
只能证明汉室官方确实有进行掩盖历史的意愿,
作为真正合格的历史研究者应该具有的共识是,这种意图对历史流传进行完全否定与抹杀扭曲的行为无疑是值得谴责的。
对于项羽本身表现出的能力与才华,如实叙述不代表就是夸大,一本合格的史书不可能不反应一定程度上的真实信息,否则史记没有理由得到后世学者的称赞和占据史学界中重要的地位。
作为合格历史研究者对这种只有全面美化统治者目的的看法本应不予支持,又怎么可以反过来指责史官的不公?
要知道史官是在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冒族人被连累的危险写书,
退一步说,即使史记确实是代表作者一家意气之言,也只能证明这是在官方意志下抹消了其他声音的结果。
至于那些联系到作者司马迁存在某些家族仇怨的观点,具体事例要靠证据与辩论具体分析不能带入个人情绪去揣度,即使存在个人恩怨也不等同必定扭曲真相,这种充满情绪化的看法不应该被视作正统研究的方法,实在是不理想不合格的历史解读眼光。
其次,为了要显得可靠有说服力,
史记必须具有适当还原历史的客观表现,
相对汉室的开创者刘邦本身,其实未必有什么实质性的扭曲污蔑可言,成王败寇的倾向早已经存在,战国时期庄子一书已有了论述。
不少史学家对成功者的不吝溢美,正体现了道德为政治服务让路,为大众行事大于个人私德的权贵思想。
后世人对于刘邦的厌恶也大多局限于表面的道德因素,而忽视了反秦的胜利果实被彻底窃取,帝制被完全承袭的影响。
史记中真正最可怕的抹黑,莫过于分封体制的成就被压抑,被“进步”的独裁帝制完全取代,
这里引用下一些值得思考的言论:“发展的眼光带来太多的隐瞒,历史进步需要一个基本恒定的标准”,项羽的未竟之功,是华夏历史中人权自由与人文精神多样发展的最大缺失,
成为华夏文明一直未能创造出媲美乃至超越城邦制文明辉煌的最大遗憾,之后的历史也变成了压抑百姓尊严与权利之暴秦制最深刻彻底的还原。
综上所述,史记对项羽的抹黑其实远大于对他的赞扬,最大程度上的赞扬充其量不过于妇人之仁这样浅薄的评价。
英雄一说也是由众多后人缅怀而来,是具有真知灼见的有志之士们从中能够联系到项羽的事迹。
以成败论英雄一直是封建体制的独裁意志大于民众心声的表现,也是代表了封建历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落后一面,是一种单纯以暴力斗争的成败取代所有实质义理批判的错误标准,如果世界历史都按照这种传统,恐怕世上要少去许多辉煌的英雄事迹,像汉尼拔拿破仑圣雄甘地等历史伟人的璀璨光辉也要被打掉不少折扣。
而关于项羽的不以成败论英雄之主体论调也不是根据官方的意愿,是凝聚了后世民心所向创造的真实心声。
项羽之所以能作为中华历史上少有的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君主式人物,许多人的意见都是认为司马迁个人对以妙笔生花的文笔对项羽进行的过度溢美。
事实上从结论上看,恰恰具有一定程度的捧杀嫌疑,首先从写作背景上可以参考下司马迁与其父辈的出身,由司马迁生父司马谈临终前对作者的一番叮嘱就可见一斑:“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他希望在死后,司马迁能继承他的事业,更不要忘记撰写史书。
如果有人认为司马迁写书是可以不需要诸多考量斟酌的,要知道史记是包含了众多人物,规模与信息量都无比巨大,不可能都来自司马迁一人之所想,其本身也是根据已成书的楚汉春秋编纂而成,绝非他的一夜独创,自然有不少可以修改加注的余地。
加上史记在后世明显有被刘向等人在东汉时期删改过的痕迹:
《后汉书。杨终传》:“终又言:“宣帝博征髃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焉。会终坐事系狱,博士赵博、校书郎班固、贾逵等,以终深晓春秋,学多异闻,表请之,终又上书自讼,即日贳出,乃得与于白虎观焉。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
从这里可以引申出一个绝非可以忽视的问题:无论史记的作者是不是司马迁,他写了多少文字,它要想存在和流传都必须通过刘汉政权的检查和认可,都必须修改到符合刘汉政权的立场。而这种立场以视为从历史的角度证明汉政权是合理合法合乎天道和天意的。
不是说史记就不能正确地反映历史真实,而是说要如何认识和看待它是怎样反映历史真实。
就其属性而言,史记无疑是当代史,是一个片面性的单方面的证词。不是不可充当证据,而是不可以将其当作史观的指导,因为史料本身就是理解的历史工具而不是唯一的证据,更不可代替史观本身。
单单就解读项羽本纪本身,就很清晰地说明了关中之约与以义帝之死发动讨逆战争的理据合法性,对于刘邦成功获取权力地位是作出了最关键的支持,而刘邦为了得到顺利继承帝制的结果,先要描写暴秦解体的直接原因,再完美诠释一个自己为何会承袭帝制的过程。
为这政治格局的变迁之中寻找一个最佳的平衡点,项羽西楚政权的存在无疑是最佳的转折点,要承袭暴秦制本身,为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就必须将项羽分封的行为证明是历史的“倒退”,从结果上瓦解分封的意义,让灭秦之功顺利转嫁到另一个成功者身上,变成继承秦制的最正当理由。
而项羽一生征战的过程,在本纪中通篇的文字里,凡是读者都很容易从多个角度找到他失败原因的一些“证明”,如残暴不仁,政治短视等,
与刘邦的对比下,项羽当时的地位无形中被高估,如鸿门宴中不少人都认为他可以直接消灭刘邦,应该直接王关中等,
也导致其能力被间接性的低估,尤其他的政治能力与谋略智慧经常被忽视,乍眼一看就好像“鼠目寸光”,很多的抹黑之词如沐猴而冠彪悍滑贼之类,也是由司马迁引用各种佐证穿插其中的安排而显得“情理之中”。
结果同样掩盖了刘邦集团同期也曾制造过的暴行,甚至可能只是一种转嫁的结果,
如秦宫的财宝最后不知所踪,始皇帝墓被盗,等等事迹。
项羽在记载上失德的每一点几乎都为后面的高祖本纪里汉高祖的成功作出诠释或注脚,这正是最精心细致的巧妙铺垫。
从灭秦之功到所谓的残暴失德,再到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只得出了欲以力征经营天下这样的苍白定性。
由此可见,真正高明的做法,不是通过对成功者大书特书的赞美,
而以适当展现失败者的种种得失成败的对比手法,作为客观真相的某种“体现”,再借此突出自己的豁达大气,包容并蓄的作风。
那些带有感情色彩描述的项羽事迹,不论是儿女情长还是优柔寡断,在当时的历史眼光中更是让他丧失了身为政治家的合格地位,留下匹夫之勇这样普通读者最容易得出的刻板印象,
从一些专门讲述男女之情的文学作品地位一贯低下就可见一斑,强调项羽重情的笔墨未必就可以跟美化等同。
至于其他细节上的表现,对他军事能力和武力上的表现,真正被隐藏战绩的应该是项羽,而不是刘邦,从法理上讲,隐藏刘邦战绩是严重污蔑,等同欺君之罪,在当时的统治环境中也没有可以实现这种暗箱操作的条件可言。
同样的七十余战,同样为帝制统治作出重大功劳的白起就显得更为耀眼立体,详鲜明细。
再联系到汉武帝执政时期对异见者的打压,
只能证明汉室官方确实有进行掩盖历史的意愿,
作为真正合格的历史研究者应该具有的共识是,这种意图对历史流传进行完全否定与抹杀扭曲的行为无疑是值得谴责的。
对于项羽本身表现出的能力与才华,如实叙述不代表就是夸大,一本合格的史书不可能不反应一定程度上的真实信息,否则史记没有理由得到后世学者的称赞和占据史学界中重要的地位。
作为合格历史研究者对这种只有全面美化统治者目的的看法本应不予支持,又怎么可以反过来指责史官的不公?
要知道史官是在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冒族人被连累的危险写书,
退一步说,即使史记确实是代表作者一家意气之言,也只能证明这是在官方意志下抹消了其他声音的结果。
至于那些联系到作者司马迁存在某些家族仇怨的观点,具体事例要靠证据与辩论具体分析不能带入个人情绪去揣度,即使存在个人恩怨也不等同必定扭曲真相,这种充满情绪化的看法不应该被视作正统研究的方法,实在是不理想不合格的历史解读眼光。
其次,为了要显得可靠有说服力,
史记必须具有适当还原历史的客观表现,
相对汉室的开创者刘邦本身,其实未必有什么实质性的扭曲污蔑可言,成王败寇的倾向早已经存在,战国时期庄子一书已有了论述。
不少史学家对成功者的不吝溢美,正体现了道德为政治服务让路,为大众行事大于个人私德的权贵思想。
后世人对于刘邦的厌恶也大多局限于表面的道德因素,而忽视了反秦的胜利果实被彻底窃取,帝制被完全承袭的影响。
史记中真正最可怕的抹黑,莫过于分封体制的成就被压抑,被“进步”的独裁帝制完全取代,
这里引用下一些值得思考的言论:“发展的眼光带来太多的隐瞒,历史进步需要一个基本恒定的标准”,项羽的未竟之功,是华夏历史中人权自由与人文精神多样发展的最大缺失,
成为华夏文明一直未能创造出媲美乃至超越城邦制文明辉煌的最大遗憾,之后的历史也变成了压抑百姓尊严与权利之暴秦制最深刻彻底的还原。
综上所述,史记对项羽的抹黑其实远大于对他的赞扬,最大程度上的赞扬充其量不过于妇人之仁这样浅薄的评价。
英雄一说也是由众多后人缅怀而来,是具有真知灼见的有志之士们从中能够联系到项羽的事迹。
以成败论英雄一直是封建体制的独裁意志大于民众心声的表现,也是代表了封建历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落后一面,是一种单纯以暴力斗争的成败取代所有实质义理批判的错误标准,如果世界历史都按照这种传统,恐怕世上要少去许多辉煌的英雄事迹,像汉尼拔拿破仑圣雄甘地等历史伟人的璀璨光辉也要被打掉不少折扣。
而关于项羽的不以成败论英雄之主体论调也不是根据官方的意愿,是凝聚了后世民心所向创造的真实心声。

 天予之霸君
天予之霸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