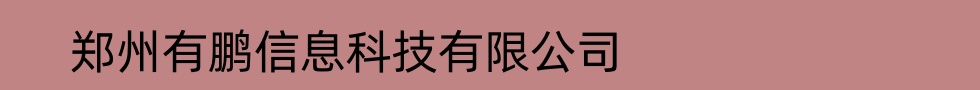十三 姐姐
范晓萱唱:“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在我的记忆里我和姐姐似乎是永远都不会老的,隔壁的爷爷奶奶一开始就是老态的,爸爸妈妈在逐渐的变老。我们住在一个大院落里,墙上的时钟滴滴答答,我跟在姐姐的身后玩的一板一眼,中午的阳光渐渐靠近,影子越来越小,我靠在她的腿上只是打了一个盹儿,千山暮雪十年的光阴都已经不在了。
十年前我住在一个僻远的乡村,姐姐在外地上学,每个周末的黄昏我都站在村口扒拉着眼睛盼望着她早点回家,十年后我混流在了人潮如织的大都会,姐姐有了自己的家,能聊的没有以前那么多,她看着我一个人辗转奔波居无安定,常常给我打电话心疼地讲:“有事弟说话。”
一 粗线条的女生
我问姐姐:“什么是楚楚动人?”
姐姐:“就是温柔。”
我:“那你一点也不动人。”
姐姐咬牙白眼瞪我。
我又问:“那什么是窈窕淑女?”
姐姐:“就是好看。”
我:“那你不是淑女。”
姐姐从椅子上弹起来拿起书本就在后面追打。
岁月做着生活利落的导演,无数风风雨雨的剪辑之后,总有一些片段会浮出记忆的水面,提醒那些你都不认为是什么幸福的场景,其实一直都是导演珍藏的惊喜彩蛋。
五岁那年,姐姐带着我去西河摸鱼,她把裤腿折到膝盖以上,拿着自制的渔网逆着河流走,我提着她的鞋在岸上亦步亦趋,她逮了鱼又漫过水草到河对岸的石块下面去捉螃蟹,我好像一直跟在后面,可不知怎么后来被冲到了河里,水流卷着我一直往下游走,还一个劲儿地往我鼻子和嘴巴里面灌,我喊着姐姐的名字,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越来越远还在弯着腰认真地捉螃蟹。像是在水里浸泡了很久,不知怎么地,我后来被一位村里的老伯牵着回了家,妈妈握着人家的手一直说感谢。
可是太阳下山了,还不见姐姐回来,妈妈由生气变成了焦急,她吃不下去饭拉着我到河边去找姐姐,妈妈在田埂上一遍一遍的叫,我顺着河流往上跑。嬉闹的孩子和放羊的老伯都回了家,夜晚的西河安静的只有潺潺的声响。
妈妈顺着我指的方向在上游对岸的一块树林里找到了姐姐,她的头埋在膝盖里,汗水湿完了头发,两个小腿被划伤了一条一条的红道子,脸上脖子上都是眼泪。她看见了妈妈,身子缩了一紧,哭着说:“我把弟弟弄丢了。”
我站在妈妈的后面,大声的喊:“姐姐,我没丢。”
晚上吃过了饭,她就把我拎到了院子里,扭扭我的脑袋,拍拍我的四肢,然后凶神恶煞的指着我的鼻子说:“到处乱跑,以后不要跟着我一起玩了,跟屁虫。”
我转身就往屋里喊:“妈,姐姐打我……”
一双手捂住了我的嘴巴。
我转过头:“带不带?”
姐姐目露凶光。
我拉着她的手嬉皮笑脸:“你逮的鱼呢?”
姐姐没好气:“全都给放了。”
我大惊:“走了那么远,那么多鱼你都给放了啊?”
姐姐嘴角含怒:“这叫放生,不懂别瞎问。”
我惋惜得叹了口气。
后来我在书中看到,放生是一种祈求亲人平安的祝愿,是救命消患的无助的祈祷。
范晓萱唱:“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在我的记忆里我和姐姐似乎是永远都不会老的,隔壁的爷爷奶奶一开始就是老态的,爸爸妈妈在逐渐的变老。我们住在一个大院落里,墙上的时钟滴滴答答,我跟在姐姐的身后玩的一板一眼,中午的阳光渐渐靠近,影子越来越小,我靠在她的腿上只是打了一个盹儿,千山暮雪十年的光阴都已经不在了。
十年前我住在一个僻远的乡村,姐姐在外地上学,每个周末的黄昏我都站在村口扒拉着眼睛盼望着她早点回家,十年后我混流在了人潮如织的大都会,姐姐有了自己的家,能聊的没有以前那么多,她看着我一个人辗转奔波居无安定,常常给我打电话心疼地讲:“有事弟说话。”
一 粗线条的女生
我问姐姐:“什么是楚楚动人?”
姐姐:“就是温柔。”
我:“那你一点也不动人。”
姐姐咬牙白眼瞪我。
我又问:“那什么是窈窕淑女?”
姐姐:“就是好看。”
我:“那你不是淑女。”
姐姐从椅子上弹起来拿起书本就在后面追打。
岁月做着生活利落的导演,无数风风雨雨的剪辑之后,总有一些片段会浮出记忆的水面,提醒那些你都不认为是什么幸福的场景,其实一直都是导演珍藏的惊喜彩蛋。
五岁那年,姐姐带着我去西河摸鱼,她把裤腿折到膝盖以上,拿着自制的渔网逆着河流走,我提着她的鞋在岸上亦步亦趋,她逮了鱼又漫过水草到河对岸的石块下面去捉螃蟹,我好像一直跟在后面,可不知怎么后来被冲到了河里,水流卷着我一直往下游走,还一个劲儿地往我鼻子和嘴巴里面灌,我喊着姐姐的名字,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越来越远还在弯着腰认真地捉螃蟹。像是在水里浸泡了很久,不知怎么地,我后来被一位村里的老伯牵着回了家,妈妈握着人家的手一直说感谢。
可是太阳下山了,还不见姐姐回来,妈妈由生气变成了焦急,她吃不下去饭拉着我到河边去找姐姐,妈妈在田埂上一遍一遍的叫,我顺着河流往上跑。嬉闹的孩子和放羊的老伯都回了家,夜晚的西河安静的只有潺潺的声响。
妈妈顺着我指的方向在上游对岸的一块树林里找到了姐姐,她的头埋在膝盖里,汗水湿完了头发,两个小腿被划伤了一条一条的红道子,脸上脖子上都是眼泪。她看见了妈妈,身子缩了一紧,哭着说:“我把弟弟弄丢了。”
我站在妈妈的后面,大声的喊:“姐姐,我没丢。”
晚上吃过了饭,她就把我拎到了院子里,扭扭我的脑袋,拍拍我的四肢,然后凶神恶煞的指着我的鼻子说:“到处乱跑,以后不要跟着我一起玩了,跟屁虫。”
我转身就往屋里喊:“妈,姐姐打我……”
一双手捂住了我的嘴巴。
我转过头:“带不带?”
姐姐目露凶光。
我拉着她的手嬉皮笑脸:“你逮的鱼呢?”
姐姐没好气:“全都给放了。”
我大惊:“走了那么远,那么多鱼你都给放了啊?”
姐姐嘴角含怒:“这叫放生,不懂别瞎问。”
我惋惜得叹了口气。
后来我在书中看到,放生是一种祈求亲人平安的祝愿,是救命消患的无助的祈祷。